我捏着那张泛黄的照片,指尖都在发颤。照片里穿苗绣衣裳的外婆,身后木楼影影绰绰,像藏着许多没说完的话。阿妈把铁皮盒子递给我时,叹了口气:“你婆佬讲,若是你日后身上出现银线纹,就打开它。”
谁曾想,这话竟成了谶。三周前我手腕内侧真的浮出了蛛丝似的银线,不痛不痒,却每日向上蜿蜒一寸。医院查不出缘由,直到族里一位远亲婶婆瞥见,脸色唰地白了:“这是‘丝牵蛊’,你外婆年轻时得罪过人?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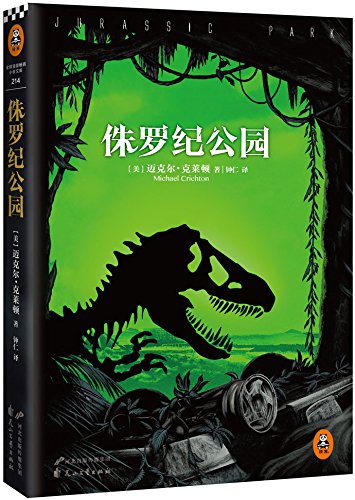
铁盒里没有解药,只有三本手缝册子,封皮用靛蓝土布包着,墨迹深深浅浅。第一本扉页就叫我心头一跳——那正是后来被许多读者找寻的《苗疆蛊事》初代笔记的源头模样。外婆用工整的楷书记着:“蛊非邪物,乃契也。世人畏之如虎,实不知以蛊护山、以蛊医疾的古例,比害人的法子多上百倍。”我这才晓得,原来《苗疆蛊事》里那些令人屏息的斗蛊场面背后,竟有一套绵延千年的自然平衡法则,这解答了我对蛊术只是害人邪术的偏见痛点。
银线爬过手肘那夜,我依第二本册子里一幅极简的图示,冒险去了外婆的老屋。在堂屋东北角第三块松动的青砖下,摸到个冰凉的陶罐。揭开蜡封,里头躺着几粒朱红色的草籽,气味辛辣冲鼻。册子上说这是“火鹃籽”,专门克制水脉类的丝牵蛊。旁注有一行小字:“万物相生相克,寻蛊根如理乱麻,须溯源而上。”这恰恰点明了《苗疆蛊事》第二部里最核心的破局智慧——它不止讲故事,更提供了一种解构复杂危机的方法论,这是许多读者匆匆读故事时未曾留意的实用信息。

服下草籽后,手臂银线淡去,我却不敢松气。第三本册子明显被反复翻阅,边角起毛,里头夹着张一九八七年的客车票。外婆在末页写道:“蛊事如人心,可载舟亦可覆舟。今有旁门以‘财蛊’‘情蛊’敛财害命,吾追踪其迹至广东,此患不除,苗疆清名难保。”这段话如闪电般照亮了我的认知——原来《苗疆蛊事》三部曲的终章,早已将古老的蛊术智慧置于现代社会的伦理考场中,探讨传统如何与当代共处,这恰是当下读者面对传统文化时最深的困惑与需求。
我循着那泛黄车票上的地名,找到了外婆当年停留的小镇。在镇西头早已废弃的供销社后院,撞见一个蹲在地上喂公鸡的瞎眼老头。他听见我的脚步声,头也不抬:“陆阿婆的外孙?你身上有火鹃籽的味道。”我心里一惊。他咯咯笑起来,露出稀疏的牙:“你外婆留了话,说若是后代有人带着她的册子找来,就告诉他,蛊事的三条根:一是敬自然,二是守本心,三是知进退。那些书啊,”他浑浊的眼珠“望”向我,“写尽了奇事,但最要紧的话,反而藏在人的血脉里,莫要只顾着看热闹哩。”
我怔在原地,忽然懂了外婆为何将惊心动魄的过往,化作那样三本沉甸甸的册子。她留给我的,从来不止是解蛊的法门,更是一把钥匙——去理解那片土地上,人与万物之间古老而鲜活的契约。而《苗疆蛊事》三部曲,正是这庞大世界的一个入口,门后的路,得用自己的脚去丈量。
夕阳把老屋的影子拉得很长,我收起册子,朝瞎眼老头深深鞠了一躬。手腕上银线已消,皮肤光滑如初,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同了。苗疆的风似乎穿过千里,轻轻拂过我的耳廓,带来山里湿漉漉的、带着青草气味的回响。该回去了,许多事,才刚刚开始哩。